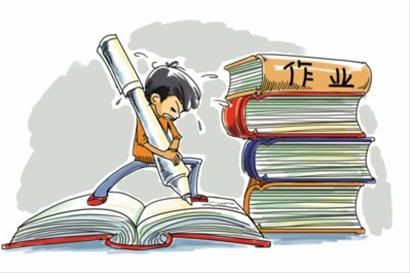日前,砂拉越一所小学传出校方禁锢学生,不让学生应考UPSR的消息,掀起满城风雨。一时间,所有矛头皆指向校方,左一句“害群之马”右一句“师道丧尽”,教育部更恫言采取“严厉的对付行动”,校长与教师一如过街老鼠。
高官们适时跳出,威风凛凛,义正言辞。教育部长丹斯里慕尤丁说,“虽然教育部为学校订下关键绩效指标,但是,学校不该在追求表现时,阻止成绩欠佳的考生参与政府考试。”教育部副部长拿督魏家祥更搬出白纸黑字,“教育部指南从不允许成绩差的学生可以豁免考试,成绩差不能成为‘免考’的藉口。”
奇怪,愚钝如我都知道,“禁锢、禁考”是不道德且犯法的。身为专业教育工作者的校长与教师若不明白这简单非常的常识,岂不叫人笑掉大牙?在杏坛混了这许多年,他们又岂不知此举被揭发的严重后果?区区一场考试,竟值得他们赌上自己的名誉、道德、操守?UPSR,真有这么厉害?
犹记2009年UPSR放榜,关丹一所小学校长因UPSR及格率偏低而落下男儿泪。隔年同期,关丹另一所小学的校长,也因学校的7A生减半而泪洒当场。在凄凄惨惨戚戚的另一边厢,则是一些学校因成绩有所进步而意气风发。只是一场考试,竟能轻易将人带上天堂,又把人推下地狱,实在叫人难以置信。
考试的“力量”其实远不止此。据我所知,不少学校为了这场“战役”,很早即开始“练兵”,而且极具针对性,考什么就练什么。考试没考的,则无需“浪费”太多时间。于是,华文、国文、英文、数学、科学成了“主科”;体育、美术、生活技能、地方研究、公民教育、道德教育等则沦为“副科”。为了让“主科”拥有更多教学时间,“副科”理所当然被牺牲。学生一整周、一整个月,甚至一整年没上体育、美术、道德等副科,已是见惯不怪。
“练兵”的针对性不只表现在为主科牺牲副科。“练兵”之细腻早发挥得淋漓尽致,程度已臻化境。若“战场”只考短枪与手榴弹,那学生就只学这两项,其他诸如长枪、机关枪、匕首、烟雾弹等可以不管。不仅如此,若只考短枪的组装技术,则换弹、上膛、发射等皆可以不理。于是,学生从年头到年尾,面对的都是一本本“量身订做”的模拟练习,日复一日年复一年,不厌其烦地一直这么操练下去。一位退休老师说得实在贴切,“六年级不都是这样?做完了讨论,讨论完再做。”虽闻之叫人心酸,却无比真实。
学生用考试来证明自己的价值;教师为了考试而教;校长以考试来决定是哭还是笑;家长根据考试评估学校;官员以考试来衡量教师的优劣。为何会发生“禁锢、禁考”的事件,应该不难理解了吧?
《国家教育哲理》列明:“教育是一项持续性的事业,它致力于全面及综合地发展个人之潜质。”《小学课程纲要》则阐明:“教师在设计教学活动时,应顾及学生的智能,设计多样化的活动。”在考试伟岸的身影下,任何教育理想皆微不足道。考试便是一切。
可台湾饭店教父严长寿先生偏爱泼冷水,“考试只容许‘有强记能力’的考生出头,考试考不出热忱,考不出责任心,考不出使命感,考不出沟通力,考不出领导力。考试当然也考不出有远见、有企图心、有决策能力的领袖。考试更考不出一个人的品格、品味,至于艺术、文化教养内涵,更是统统考不出。”
我耳根发热、气急败坏:“那……那……那……那又怎样?”
此文刊登于:《联合日报》30.9.2011